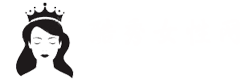《大秦文萃》 2022年361期 ▍总1853期

夜里起风了,沟圈里被毫无征兆的大风刮得十分干净,天刚亮,我下沟摘桑叶,却在苹果园的树叶里意外看见一双滴流乱转的小眼睛。这双眼睛我非常熟悉,是村东头碎狗爷家的公牛,公牛潮乎乎的眼里有血丝,他好像一夜没有睡。“你咋在这哒?”我吃惊地问他。公牛把手指放在腊肠一样的厚嘴唇上小声说:“日你先人,你轻点,我昨晚守了一夜黑,看西洋镜呢。”我被公牛拽进他用树枝搭建的隐蔽所里,我感觉公牛异常兴奋,兴奋得有点不正常。公牛说:“你娃来的不是时候,牛二已经睡了,刚才呼噜还像打雷一样响,现在却没有声音。”我问他:“你看啥西洋景?”公牛说:“嘘,看狗练蛋。”我说:“牛二叔的那条破狗早已死了,看啥狗练蛋呢?”公牛说:“是人练蛋,比狗练蛋看着过瘾。”我觉得公牛说这话有点太流氓,不想靠近他。他却使劲按住我的肩膀,不让我动弹。我说:“我家的桑叶,夜黑里蚕吃完了,一大早仰扬起头齐刷刷看我,我得去摘桑叶,我要对蚕负责任。你看你的,我趁牛二叔现在睡觉,我去偷桑叶呀。”公牛跳起来瞪圆眼睛:“你娃敢去,看我不捏碎你的卵蛋。”我有点怕他,他比我有力气,他捏住卵蛋一般不松手,每次我只能跪下来喊他爷,他才肯丢手。我应该管公牛叫叔,我从来不叫他,他比我大四岁,是我们乾村里的百事通。他啥都知道,脑子里却是一锅浆糊,念不进去书,矮胖敦实得像沟里的狗尾巴草,一路野蛮疯长。用我爸的话说,公牛就不是念书的材料,是一个跟在牛后面扛铁锨的货。我不这样看,他在我的心中就是和牛跟头爷一样,将来一定会成为英雄的。牛跟头爷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大英雄,他是公牛他碎爷。

听老村长爷说,民国十八年,土匪跋扈,在村里闹事,一干人围住从口外回来的福田家的窑门,放一枪吓得福田爷尿湿裤裆。土匪用黑乎乎的枪口抵住福田爷的脑袋,逼迫福田交出从口外带回来的银元。那一夜,风疾如刀,声音刺耳,全村人龟缩在炕上不敢出声。牛跟头爷从黑影里闪出来,从骡子上揪下匪首,双手举起来挂在村口的皂角树上,土匪的短枪掉落在地上,人都没有看清,风一样的黑影忽的消失在夜幕里,吓得匪首屎尿从裤腿里哗哗往下流。牛跟头爷名扬沟圈内外,凶悍的土匪抢劫洗村都绕着村子走,他们不敢进村,土匪知道乾村里有高人。我一直认为,公牛继承了牛跟头爷的基因。“出来了,出来了,看牛二出来了。”我顺着公牛手指的方向,看见牛二叔出来站在窑门口伸懒腰。牛二叔站在天井的草丛里撒尿,这泡尿尿的时间很长。牛二叔穿白粗布大裆短裤,没有勒裤带,他是把裤子一折别在腰里的。我的尿脬有点涨,想撒尿,公牛拽住我不让我喘气。牛二叔好不容易尿完,站在院井里伸手朝天哈气,没有裤带管束的裤子忽的就掉在脚腕上。牛二叔弯下腰提裤子,白晃晃的屁股蛋子正对着我们。我奇怪牛二叔青铜色一样的上身,捂在裤子里的屁股蛋咋就这么白呢?公牛却说:“昨夜晚牛二太狠了,早上起来裤子都提不起来了。”我吃吃笑。这时候,牛三叔站在沟圈上面朝沟里喊:“牛二,牛二,时间到啦!”牛二叔回应:“到啦,老三,你来!”牛二叔进窑里,牛三叔立在天井院厅里等。牛三叔今日个穿戴周正,这么热的天穿一身褪了色,有点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头上扣一顶帽檐耷拉黛青色的帽子。

牛二叔从窑里出来,手里牵一个黑黑的女人,这个女人我前几天见过,在乾村街道上要饭。我当时没有看清眉目,只觉得她是一个要饭的外乡人,她看起来也有四十多岁的年纪。昨夜里咋就进了牛二叔的窑里,今天牛二叔却要交把她交给牛三叔?女人在牛二叔的手里挣脱几下,显然她没有牛二叔的力气大,牛二把她交给牛三,牛三拽她,她拱着腚不走,她“拧次”许久,还是被牛三拽着走了。女人被牛三拽着走,一路上了沟圈,两人撕扯着往牛三住的那个窑洞里走。牛三嫌女人走得慢,扛麻袋一样将女人放在肩上“蹬蹬”进了他的破窑洞。公牛站起来对我说:“走,去牛三那个沟里看牛三和那个女人干啥呢,估计热闹得很。”我说:“我不去,我要去学校上学,我摘几把桑叶就去上学。”公牛说:“上那个破学,念那些破书,到头来还不是跟在牛后面扛铁锨。我给你算过,好像,你娃将来不一定比过牛二。还不如现在去看牛三和女人在窑里弄啥呢。”公牛用了一个“好像”的词语,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来的,记得在学校念书,老师让他用好像造句,他说:太阳好像一个烙熟的锅盔,月亮是锅里炕糊了,被我爸咬一口的死面饼子。老师笑,同学们也笑,公牛却不笑,这个笑话,成为乾村经典的段子。公牛和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身边有一股风刮过来,我站起来一闪身,牛二叔蒲扇一样的大手扇在公牛的脸上,公牛被牛二扇得一趔趄。牛二拧住公牛的耳朵,公牛杀猪一样喊:“哥,疼,耳朵掉啦。”牛二拧住公牛的耳朵厉声问:“日你先人,昨晚上是你在苹果园子藏着,就说夜里有响动,我以为黄鼠狼闹窝呢,原来是你个哈锤子。”公牛说:“我没有,我没有偷苹果,我夜黑里听你和女人睡觉哩。”牛二生气了,踢了公牛一脚,硬说公牛昨晚偷吃苹果了,要把他往队长哪儿送。我站在一旁,吓得大气不敢喘,对牛二说:“二叔,我爸早上让我摘桑叶,喂我家蚕的,我才来么。”牛二叔对我说:“你摘你的桑叶,今后,不要和这个小王八羔子混在一起,他是咱村里的祸害。”牛二叔用手拧着公牛的耳朵往沟圈上走,还不忘回头嘱咐我:“你摘完桑叶,上学去。”我结结巴巴说,是是是。

我在沟里胡乱扯几把桑叶,心急手也慢,手上划一道口子,有鲜血流出来了。我急着跑回家用锅灰涂了伤口,放下桑叶,贼一样背上书包去村里小学念书。我爸起床了,他在大门口吃旱烟,他截住我问:“昨黑里,你去你二叔哪里听窑了?”我说:“我没有,一早上我去给蚕扯桑叶来。”我爸说:“小孩子,不要偷听你二叔的窑。你二叔也不容易,弟兄两个,四根干柴棒也够恓惶的。”上午是语文课,福俊老师讲《苹果熟了的时候》,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好不容易捱到放学,我急着回家找公牛打探消息,急匆匆往家赶。谷子地里忽然窜出公牛来,他小学念书4年,实在念不下去,就在村里瞎晃荡,我看见突然从谷子地里跳出的公牛,兴奋地围着他转圈,怎么,公牛脸上挨打的巴掌印子不见了,走路却是一瘸一拐的。我问他:“队长咋说哩?”公牛说:“咱们村风水不好,弟兄两个娶一个女人,轮流睡,还不叫人说。牛二给队长说我偷生产队的苹果,队长也信,我爸也信。队长骂我几句,我爸用他的弹簧腿踢得我屁股蛋疼。我爸说,狗日的,如果再去偷苹果就送你去塬上挖煤。”我说:“挖煤就挖煤,有工资呢,能吃白面馍馍。”公牛说:“你知道个辣子,下煤窑是把命别在裤腰带上的。我不去,我还没有娶女人哩,万一那天死在井下,冤枉死了。”我说:“公牛,你一天就知道学坏,我爸说,牛二叔也恓惶,两个光棍四根干柴木棍。”公牛却说:“屁,一个女人两个人轮流睡,这是共产共妻吗?”那年公牛11岁,我7岁。夜里,队长二爷喊我爸去窑里开会,来人说有重要事情商量,不让告诉碎娃们,碎娃们嘴不严实,容易走漏风声。我在家里写作业,我爸走的时候给我的房门落了锁,我写完作业拍门喊要尿尿。我妈在门外面说:“你爸不让你出门,想尿就尿在壶里。”其实,我不太想尿尿,是想去问问公牛,夜里生产队开会,牛二、牛三的婚姻大事总得有个结局呵。写完作业,我躺在炕上饭“翻烧饼”,夜里听见我爸和我妈说话。我妈说:“给牛二收留下一个要饭的做媳妇,也是不错的,那女人我见过,屁股大,底盘结实,能生养娃娃。只是弟兄两个娶一个媳妇,这咋能成,这不成旧社会了?”我爸说:“可不是?公牛昨黑里躲在苹果园里听窑,牛二拧公牛的耳朵在街道上一闹,怕是要犯法的。今黑里开会,队长说了,先给牛二办手续,后面有茬口,给牛三拾掇一个媳妇。”我妈说:“这个办法好哩。”我爸说:“好个屁,那个女人却不愿意了,她说她的男人年前死了,咱们这哒地广人稀,能混饱肚子。女人说她的家里还有一个丫头子,她要嫁,就要名门正娶,要一口袋麦子做彩礼。”我妈说:“这难场啊,牛二一家没有爸妈,谁给主张哩。”我爸说:“不难场,各家各户给凑一下,能救眼前的饥荒。”我妈说:“有个丫头子也好,省得牛二无后。”我实在困得不行,一觉睡到天亮,早上我走在村道上,看见各家各户从家里提麦子在队长门前过称。我揉揉眼睛,觉得昨黑里我爸和我妈的对话不像是梦。

后晌放学回来,我提笼去沟边捉猪草,在沟边遇见牛二叔,牛二叔蹲在沟边吃旱烟。我说:“二叔,你看苹果呢。”牛二说:“今日个学校教的啥?”我说:“二叔,学的是《苹果熟了的时候》。”牛二叔起身对我说:“队里的苹果还是青蛋蛋,苹果熟了,你来,叔给你摘几个尝尝。”我说:“嗯呐。”牛二叔下沟坐在院井里吃旱烟,我在沟圈上面捉猪草,猪草快要放满竹笼的时候,有人从后面掐住我的脖子,我回不了头,我大喊:“妖魔鬼怪快现身,要不本大侠就杀回马枪了。”那个人还是不松手,我伸手从后面一把掏住那人的卵蛋,使劲捏,那人在后面叫起来,我一听就是是公牛的公鸡嗓子,我越不丢手。公牛疼得跪在地上求饶。我逮住机会让他喊我爷爷,公牛起先不肯,我一用劲,他大声喊:“爷,爷,你松手啊,蛋碎了。”我一松手,公牛就扑上来把我压在身下,用一根狗尾巴草往我鼻孔塞,我打了一个喷嚏,一口痰吐在他的脸上。公牛翻身下来,用袖口擦掉白痰,厉声问我:“你从哪儿学会掏裆了。”我说:“在我六舅德全哪儿学的?”公牛一听就蔫了,德全是我六舅,他是沟圈之内有名的拳师,打洪拳的,整个沟圈的半大小子都是他的徒弟。神通广大的公牛应该知道。我问公牛:“你娃服不服?”公牛跪在地上说:“我服。”公牛躺在地里给我说:“晌午和我爸去除草,听我爸说,那个黑女人走了。”我说:“哪一个黑女人?”公牛说:“牛二、牛三共同娶的女人么。”我说:“我听我爸说,那个女人回家办手续去了。”公牛有点生气,站起来说:“我们家还给随了五斤麦子,我爸让我下一个月吃高粱馍馍,高粱馍馍吃了拉不下屎,一拉屎痔疮就出来。我爸也是的,那个牛二冤枉我,他不主张正义,还打我,你说,到时候还得给牛二随礼,他脑袋让门挤了。”那个黑女人走后,就再没有音信,村里人说队长和乾村的人都让那个女人骗了,当初就不应该放那个女人走。我看出来了,队长二爷走在村道上披一个招风的夹袄,他手背在后面,在村里骂鸡骂狗,骂公牛不是一个东西。我们碎娃们吓得都不敢出门了。我妈对我说:“这几日,你队长爷毛了,你们碎娃不要去招惹他。”晚上,我老实待在家里写作业,听见窑门口有公鸡打鸣的声音,正疑惑天黑了公鸡还打鸣,一想,是公牛给我打暗号哩。我对我妈说:“妈,我去同学家借橡皮啊。”我出了大门,看见公牛兴奋的表情,就知道乾村出新闻了。公牛说:“那个黑女人回来了,在队长家里,还领来一个碎女娃。”我妈在院里喊我:“跟弟,大人的事情,碎娃操什么心,小心你爸回来打断你的腿。”

我害怕我爸打断我的腿,让公牛去打听消息,叮咛他有消息随时播报。乾村有新闻了,我却不能到场,正急的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我妈却长吁短叹,一个人自言自语:“女人也恓惶,不恓惶谁愿意嫁给牛二。牛家兄弟家里大水冲洗过一样,连个鸟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住在沟圈里的烂窑里,给队里看苹果,唉。”我妈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我爸晚上去队长家里商量事,我写完作业,躺在炕上等我爸回来,实在困得不行,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半夜起来听我爸给我妈说话:“那个女人来是来了,还带一个碎女子,这一回女人变卦了,她死活不嫁牛二了,要嫁给牛三。队长不同意,大麦没有黄,小麦咋能黄。牛三却不愿意要她了,你说,牛二41岁,牛三38岁,嫁给谁光景能过好吗?”我妈没有发表意见,她嘟囔着说:“睡觉,明日个要起早收菜籽哩。”我爸不再言语,一会儿翻身就打起呼噜。我妈翻来翻去一晚上没有睡踏实。我想,我妈对这桩婚姻是不看好的。事后,听公牛说,那个黑女人没有嫁给牛家两兄弟,而是选择嫁给坡上面的跛子。那个跛子叔有手艺是个皮匠,比牛二叔年龄还大,我见过他,他右腿膝盖上绑一个皮子做的垫子,走路用右手撑着皮垫子走路,一跳一跳的像在跳舞。我过去和公牛一起上学,公牛看见拐子叔,跟在后面喊他:“铁拐李,路不平。”那个跛子叔追不上公牛,就把公牛记住在心里:“你娃娃,不要落在我的手里,我迟早要掐烂你的卵蛋不可。”公牛也有点大意,有一天被拐子叔逮住,拐子叔手劲很大,捏得公牛叫爷也不行。他用皮绳拴住公牛,让公牛打扫窑里的卫生,把院井拾掇干净才放他走。后来公牛告诉他爸,他爸失及慌忙上坡上去找过那个跛子,两人闹得很不愉快,以至于后来公牛家杀羊,去坡上熟皮子,拐子叔不肯给他家熟,老说忙,顾不上。秋天包谷成熟了,今年雨水多,包谷成熟得有点晚,十月一过,村里人急着在地里掰包谷,赶节气要种麦子。全村都忙,我们家人手不够,我爸喊牛二叔来我家帮忙掰包谷。后晌,我妈给牛二叔做的是扯面,牛二叔蹴在我家大门口的青石上吃面。牛二叔吃面有他的固定程序。牛二叔单手端着粗糙的耀州老碗,老碗釉面上没有花纹,碗沿上一圈黛青色蓝线,碗与手的夹缝里夹一片炕得有点过,有点糊的锅盔,他左手端一茶垢秀满的搪瓷缸子,里面半缸子陕青茶梗,没有多少叶子,水是满着的,冒着热气。二叔端着的老碗里,是一筷子厚的扯面,面条一根一根麻绳一样盘在碗里。面上一定是撒了一把葱花,葱花上铺一勺辣椒面,用滚油泼了(滋啦一声我在院子能听见),冒着香气,面比碗高,头比碗大。牛二叔赤裸着青铜色的上身,脊背上泛着白颜色的汗渍,黑颜色的粗布裤子挽着,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矮,刀削般直立着的耳朵背后夹一根手指一样粗的手工卷成的旱烟,二叔双腿分开,铁塔一样立在门前。二叔放下茶缸,用一指厚的锅盔盖在茶缸上。牛二叔把老碗用力一戳,碗就立在青石的中央。二叔从裤兜里掏出一轱辘生蒜,把蒜放在掌心用手一拍,粗糙的两手来回用力搓揉,边搓边用嘴吹蒜皮。蒜剥好了,二叔开始用筷子搅动一碗山一样的扯面。二叔用筷子搅面,胳膊上的腱子肉一上一下在动,宽阔的后背捶布石一样平展。 二叔搅面的时候嘴是张开着的,眼睛死盯着碗里的面。筷子在老碗里转圈,二叔的嘴一张一合,一下,两下,三下,面在碗里变成了猩红的颜色,看起来诱人得很,馋人得很。我双腿抱膝用下巴支在膝盖上,一眼不眨,欣赏蹲在门前青石头上准备吃面的牛二叔。牛二叔端起老碗,开始吃面。开始吃面的二叔把筷子伸进碗里,使劲一挖,筷子一转,原本立在碗里的扯面就被挑起来挂在筷子上。二叔有点夸张地把面举过了脑袋,筷子一下落,一拐弯,一筷子面就送进嘴里。二叔钢牙一合,两腮就鼓起来了,一仰头也不咀嚼,喉结一动,一筷子面就通过食管囫囵到了他的胃里了。牛二叔吃面的时候,泛青的光头是偏着的,一整套动作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风卷残云一般。看二叔吃第一口面的时候,我一下兴奋起来,选择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就在我换个姿势的这会功夫,我吃惊地发现二叔尖尖的老碗塌陷下去,只剩下可伶的半碗面在碗里了。我揉揉眼睛,心里说,等等,我还没有看清呢。我来不及咽一下口水,二叔,你的半碗面就秋风扫落叶一样席卷成半碗了。二叔吃面,一口面一瓣蒜,面不用咀嚼,蒜“咔嚓”几下,囫囵下肚,接着第二筷子面就从碗里挑起,猩红的瀑布一样挂在他的嘴边。看二叔激情澎湃吃面,我有点饿了,肚子的馋虫在咕咕叫,口水滴在手背上,干瘦的,杏叶一样大的(我妈对我儿时的称呼)脸上写满羡慕。有半碗面垫底,接下来牛二叔吃面就不那么急了。一根一根从碗里挑起来,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二叔开始咂摸扯面的味道,这段时间有点长。二叔吃面时间越长,对我就是一种折磨,我想牛二叔肯定也是这么想的。牛二叔用很长的时间,夸张地一根一根吃完剩下的半碗面,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碗,二叔舔碗是把整张脸埋在老碗里的。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舔碗这个动作,没有人能做到牛二叔那么干净彻底。舔完碗,二叔用手抹一下嘴,在鞋底上一抹,吃面就接近尾声了。吃完面的牛二叔放下老碗,开始满足地喝茶,二叔一口茶一口锅盔,腮帮子慢慢在动。吃完锅盔,惊心动魄地吃面就进入垃圾时间,这时候牛二叔看起来就有点慵懒,一点也不好看,缺乏画面感和带入感。牛二叔用茶水勾完缝子,站起来跳了一下。我想,二叔是想让那碗扯面更加扎实地压在一起,让一根一根扯面慢慢抵抗夜里随时袭来的饥饿感。吃完面的牛二叔开始抽烟,抽烟的二叔蹲在地上一动不动,像矮了半截的门板,在我家门前蹲成了一尊雕像,看不清轮廓,只有黑夜里的烟头一明一暗。我收完牛二叔的老碗送给我妈,发现我爸在厨房啃包谷,我妈做的两个人的饭让牛二叔一个人咥光了。夜里做梦梦见我也在吃面,吃的是白麦面,在夜里嘴一直吧唧。我和牛二叔比赛吃面,他吃一老碗,我吃一老碗,实在撑不住了,我开始喝水,二叔却在喝茶。晚上起来尿尿,我妈说:“我娃昨日看牛二吃面,夜里做梦也在吃面,看把我娃馋的。”我不承认,后来再提起这些事,我妈就抹眼泪,我就不提这事了。那个黑女人也算仗义,嫁给跛子后,从老家领来一个18岁的女子叫杏秀,说是给牛三叔介绍的媳妇。队长二爷这一回坚持原则,说啥不能让杏秀和牛三圆房,得先住下,像种瓜一样,成熟了才能吃,要么夹生。队长爷的意思是说,两个人王八对绿豆看对眼了,就算成熟了,再结婚也不迟。 公牛却对我说:“村长懂法?还不是上一次让派出所叫去了,他怕了。牛三也不敢明目张胆扛杏秀去他的窑里,那是犯法的。”我说:“你僻远,小心牛二叔扇你娃耳巴子。”公牛有点怕牛二,也不敢招惹杏秀的,但是他遇见坡上跛子,却跟在后面继续喊:天上下雨地下流,牛二睡了,牛三睡,最后留给铁拐李。这话让牛二听进耳朵,牛二撵了一天公牛,在沟里撵上后,压倒美美捶了一顿,公牛再遇见那个黑女人,再也不敢张扬了,低头顺眉叫嫂子你好。这以后,牛家两兄弟和黑女人的故事就成为乾村的天大的秘密,大人们说,以后打死也不能往外说。从那以后,乾村就没有人提起那件事情,那件事情在乾村就如同天外忽然飘来的一朵云彩,云是飘走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公牛那张破嘴里说的流水的老婆跟本不存在。这时候,公牛也开始有了变化,村中的碎狗爷老是手里提一根鞭子见面就抽他,他从此再也不敢招惹牛二了,他不说,牛二、牛三两弟兄和黑女人的事情就成为乾村的历史了。 我却和杏秀姐熟悉起来。杏秀姐住在我家隔壁,那是村里杀猪的十爷的房子,十爷是一个绝户,十爷死了就空下来了。队长爷让杏秀先住在哪儿,让她参加生产队里劳动。队里派人从陕南把她的户口给迁在乾村。杏秀是一个清秀的女子,长长的头发黝黑黝黑的,皮肤也白,不像我们乾村的人。那时候,我已经上五年级,10岁以上的娃伙也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暑假里,生产队在塬上平整土地,我帮忙推车,掀车,杏秀姐和我一组。有一天我帮杏秀用铁锨铲土,杏秀姐不让。她说:我不敢让知识分子累坏身子,影响学业。两个人在争抢中。我碰到杏秀姐的胸脯,那是一对富有弹性的欢蹦乱跳的兔子,杏秀姐红了脸,我一下楞能在哪儿,觉得我有点像公牛一样耍流氓。我心里说:杏秀姐,我不是故意的,杏秀姐却一点也没有在意,我却深深自责,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流氓了。 生产队体力活重,有时候,牛三叔也过来帮杏秀干活,牛三叔过去邋遢,现在衣服也洗得也干净。杏秀姐来队里一年了,队长爷考虑要给她和牛三叔圆房,杏秀姐却有了想法,她不愿意跟牛三叔了。队里让我妈问缘由,我妈也问不出来子丑寅卯来。队里觉得牛三叔有点窝囊,就安排牛三叔在队里的铁匠铺上班,那个地方只要有力气能多挣工分。生产队里的铁匠铺,在福田叔家里地窑天井里,打一些农具,后来给城里工厂加工螺丝,年底能分一百多元钱。打铁成为村子小伙们梦寐以求的职业。福田叔家里的铁匠铺用篾席搭成的草棚下就是打铁的地方,一个炭火炉子和一个打铁用的砧子。铁砧子有百十来斤沉,每天临睡之前,福田叔每天夜里封好炉子,都要对着铁砧子仔细看,他必须记住铁砧子的位置,负责第二天天亮,铁砧子夜里会自己跑路,要么在窑口,要么在大门口做档门石。有天夜里福田叔起来撒尿,他看见牛三叔用布条绑了砧子用嘴叼起满院走,气不喘,脚不飘。福田叔知道他一身的蛮力藏在宽大的黑袄黑棉裤里,有劲没处使。牛三叔在铁匠铺上班,公分挣得多,有一身力气。有一次生产队里的公牛忽然发疯,拉着犁铧在村道上狂奔。事后听公牛说,那天是他吆牛扶犁耕地,一鞭子打惊了牛,他在后面追,发疯的牛在村道上奔跑,刚好遇见穿大红衣服的杏秀姐,牛一头奔了过去。眼看要出事了。牛三叔出手了,他一把推开发疯的公牛,奔跑的牛楞了,杏秀姐也楞了,跟在后面的公牛说他脸吓得惨白,多亏牛三叔神力,牛三叔这一推,成为公牛在我耳边老提起的,语文课本上的刘英俊拦烈马一样的英雄。这段故事,后来也成为我们乾村的传奇。生产队有时候下工迟,我妈叫杏秀姐过来吃饭,杏秀姐也勤快,洗锅洗碗,打扫卫生和我说说笑笑。晚上我写作业,闲下来的杏秀姐在旁边看我,有时候,杏秀姐让我给她家里写信,两人挨得有点近,杏秀姐的头发就搭在我的脸上,我抬头一看,看见杏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我们两个都红了脸。一年后,生产队要给杏秀和牛三叔举办婚礼。我听到消息后给我妈说:“不许杏秀姐和牛三结婚,我要娶她。”我妈一下笑起来,拍手给我爸说:“你看看,你家跟弟娃说他要娶杏秀的。”我爸摸我的头说:“你要娶杏秀?胡闹。”我说:“我是认真的,你们大人却当成笑话听。”大人们谁也不听我一个碎娃的话,继续操办牛二叔和杏秀的婚礼。事后,听我妈说,这次是杏秀姐提出的,牛三叔没有提。 他们两个到底要在我家隔壁,我的眼皮底下结婚了,有点太欺负人了。我有点生气,发誓不再理杏秀姐了,也对牛三叔开始充满了敌意。他长得猪头一样,他不配杏秀姐的。我爸让我给杏秀结婚写对联,我记得我写的是:招引凤凰陕南来,关中牛三乐开怀,横批是:天作之合。有一天过年写对联,猛然想起这个事情,我告诉妻子,她笑得弯下了腰,她说:“你也觉醒得也太早了,不到十二岁就想结婚了。”我说:“我那时候是真心的,每天都在想漂亮的杏秀姐要嫁给光棍牛三叔,她不配杏秀姐,我那时杀他的心都有了,却不敢动手,我惧怕牛三叔那身力气。”我给爱人说:“杏秀姐和牛三叔结婚那天,公牛过来拉我去听房,我有点愤怒,和公牛打了一架。那次公牛没有打过我,公牛发誓要和我割袍断义,永不联系。”我站在大门口呸他:“谁稀罕,一个大公牛,一个骚公猪。”杏秀和牛三叔结了婚,我的杏秀姐到底嫁给牛三叔了,哪一年牛三叔40岁,杏秀姐19岁。我在杏秀姐结婚的那天晚上,没有吃筵席,一个人在沟边哭了很久。我在沟边骂我妈给杏秀姐做工作,骂我爸给杏秀姐家里送麦子,骂村长爷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让杏秀姐那么懂事的人,嫁给一个啥也不是的老光棍牛三。全村都觉得这桩婚姻美满,只有我一个人认为全乾村都病了,连同爱抱打不平的公牛,他也无耻地认为牛三叔和杏秀是天作之合。我在沟边看见落寞的牛二叔在沟里的院井里吃旱烟,我的心才平衡下来,整个乾村就我们两个人,在这一晚上很落寞。牛三叔和杏秀姐结婚后,牛三叔在大门口栽下三颗泡桐树,有一颗疯狂长,另外两颗慢悠悠在观望就是不长。这之后,我考上高中去城里上学,很少看见杏秀姐,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老躲着她,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也许是一种心理上的不甘吧,现在想想,也不全是。再后来,我学业忙,经常看不见杏秀姐,有时候回家拿馍,听我妈说,杏秀生了一个丫头子,我却没有见过,老是见到牛三叔蹲在大门口吃旱烟。有一次,我在县里中学大门口遇见牛二叔,牛二叔满目沧桑,看起来不像40来岁的中年人。后来,我上大学在城里工作,听不到乾村的消息,有一次回家问起杏秀姐。我妈叹口气说:“你村长爷年前死了,没有人给牛三张罗婚姻了。”我奇怪地问到:“不是有杏秀姐吗?”我妈说:“杏秀早就走了,不知道啥原因,两个人老是打架,最后杏秀赌气走了,都几年了。”有一次过年回家,我看见牛三叔一个人蹲在门前吃旱烟。我和牛三叔打招呼,牛三叔夜里在隔壁喊我。我妈说,你过去陪陪你三叔。我过去后,牛三叔在锅里煮五斤猪肉,切大块给我放在碗里。那一晚牛二叔也来了。我们三个人大碗喝酒,酒量很好的牛三叔却喝醉了,喝醉了牛三叔,捶胸顿足,骂自己不是东西,对不起杏秀母女。我和牛二叔也不言语,只能默默流泪,也不劝他,我们两个那个时候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劝他才合适。这几年乾村变换也大,今冬,从城里回来在村里找儿时的玩伴公牛,刚好遇见公牛娶媳妇。大家猜,他娶的是谁?是坡上面跛子的女子,应该说,黑女人带来的丫头,她过去和我在一个班上学,上完小学就再没有上,过去公牛老是跟在女娃后面喊:天上下雨娘家人,生个女子不是人。时空变幻也太快,公牛今天要娶的这个女人,就是他嘴里经常骂的女子。确切的说,是黑女人领来的那个丫头子。我在婚礼现场终于看清黑女人带来的丫头子,长得和黑女人一样结实。公牛却依旧满身匪气,穿新西服扎红颜色的领带,一见我就过来要掐我的卵蛋,也不顾及我身边的爱人。我跳开骂他,你就是一个下三滥的货。婚礼正式开始,我却看见牛二叔和黑女人坐在主宾位置上,公牛在台上叫两人爸妈。我才明白,坡上跛子死后黑女人嫁给牛二叔了,黑女人和跛子生的那个男娃,怎么看就像坐在主宾席上的牛二叔。真是不像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牛三叔却因杏秀不辞而别,再也未娶,整日借酒消愁。听我妈微信里说,前一阵牛三去世了。村里人用他栽种在门前的一人搂不住的泡桐树作了棺材,我记得是牛三叔自己栽种的桐树。我家隔壁成了空院子,我妈打电话说,昨日里你爸放倒界墙,两家终于成为一家了,地方宽敞显亮。我却在电话里发起脾气“你放人家界墙干吗?杏秀说不定会回来的。”我妈说:“杏秀都走10年了,她是不会回来的。”有一天,我去一个煤城采访,在一家陕南小吃店吃饭。我要了一碗热面皮,一碗菜豆腐,在午后灰沉沉的空气中吃饭。这阵儿过了饭点,食客也不是很多,我无聊地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突然有服务员送给我一瓶汽水。我看着汽水,突然想起我上学回来,用捡瓶子挣来的钱给杏秀姐买了一瓶汽水,杏秀姐就是不要,她银铃般的笑声仿佛就在我的耳旁。我抬头看时,那个个头不高皮肤很好的,白皙的年轻女娃,活脱脱就是我N年前见过的杏秀姐。 女娃见我一个劲看她,回身从操作间叫出一个中年妇女,中年妇女站在我的面前,看我许久,她说:“你是乾村的跟弟吗?”我点头说是,那个女人说她是杏秀。我看着有点沧桑的杏秀,半天没有说话。杏秀却哭了。我说:“牛三叔终生未娶,前年得病死了。”她说:“过去一言难尽呐。”再后来,听我妈说:牛三结婚后,可怜牛二,要杏秀和牛二也睡,她不肯,这啥风俗,把人当成牲口了。我给我妈说,那不真实,只是一个传说。(原文刊登在《黄河》杂志上)关于本小说的一点思考·邹冰
进入中年之后,我越来越发现我写不了小说,我写出的小说都是生活的原生态。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突然想到一个题目,一句话,一件故乡的事,就不由自己,提笔就顺畅地往下写。写罢再看,写出的东西由性而走,竟然和生活里发生的一模一样。小说里的人物哭,我也会哭,小说里的人物笑,我也笑。
爱人说:看来你是老了,有点多愁善感。
我想,也是。
我写故乡的散文,写乾村,每次写着写着,就会写成四不像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小说还是纪实。我写的都是生活里的原本,中间没有想技巧性的东西。明知道写得跑偏了,还是傻傻地写出来。我老认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原本被小说精彩多了。比如说生活里杏秀姐,她最终还是回到乾村,善良的村民给她新批了庄基,她在村里盖了几间瓦房,她给女儿招了一个上门女婿。每年回乾村,我没有和她打过招呼,只是远远地看她,她依旧开心地面对每天日出日落的生活。
人生是一场与苦难的过程,你不知道你会遇见什么事情,而这些事情你做好防备了,你准备好了,事情却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去发展。这个过程有时候撕心裂肺,肝肠寸断,谁也解释不清楚生活中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为什么会那样发展,会是那样的结局。我想存在就有他合理的地方。包括人性。随着日出日落在变化,有些变化我是不愿意放在记忆里的,怕猛然被勾起,又伤害自己一次。包括自己走过的麦城,受煎熬的过程。
我写过不少小说,天马行空,不受约束,想到哪儿写在哪儿,很少对自己有限制,也未曾加入什么作家协会,总觉得做文学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弄一个组织,几个人凑在一起,就能写出伟大生活的全部吗?
因此,我的小说发表寥寥,形不成波澜,但总认为自己抱着真诚去写的。
我也思考什么是婚姻,什么是爱情,这个题目太大,我解答不了,我经常打心眼里赞美中国女性的伟大。 女人在认识男人之前没有吃过男人家里一粒米,没有喝过男人家里的一碗水,当她决定和一个陌生男人交往的时候,是抱着多大的勇气呵。
女人本身就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女人和男人走进婚姻殿堂就长在男人的身体里啦,分也分不开。
女人认命,男人也得认命。
特别是那些在苦难中,舍身救全家的女性,必须得到赞美。她们,或者她,宁愿自己受委屈,选择和不般配的陌生男人生活在一起。比如,为了国家宁愿嫁给外夷的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女性,她们往往比男人表现得更加忘我和具有牺牲精神。
因此,就有了我写的,流水的老婆,铁打的村庄。
作·者·简·介
邹冰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甘肃作家协会会员 陕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华散文一等奖获得者
作者往期精彩回顾:
土狗天天
真诚——宋晓彬散文特色赏析
阅透人生知纸厚 踏遍世路觉山平
雨中观荷
诗经合阳秋正浓
难以割舍的依旧是火热的军旅生涯
优雅
人邻(记忆里的关中农村之六)
表兄的雄心(记忆里的关中农村之五)
二姑的理想婚姻(记忆里的关中农村之四)
白先生(记忆里的关中农村之三)
那个饥饿的人
我们村最后一个地主
欠账还钱告老还乡与农民进城
不一样的辋川烟云
生死契阔
大雪如梦
我把酸楚留在北塬上
小说|空戏(上)(下)
散文|漠谷河,夹道沟
散文|太白山下春意图
流水的日子
解锁
浪漫爱情
走马观乾陵
仰望井冈
西安的夏天
或者是一段记忆
西安·初雪(外一篇)
两性知识:送男生们一句话吧,虽然有点old:女人永远不会忘记、甚至会一生爱着自己的第一个男人。或者自己买个yuu虎牙妹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