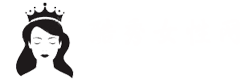坟墓包围着的艾滋病村庄。关于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很多人都以为是共用针头。又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即将来临,说说一直以来被误解的病因和 海外反动势力借这件事常年恶意诋毁的中国。
一 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一般都知道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是因为卖血。卖血怎么会感染艾滋病?大多人以为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
如果再问:怎么会大面积传播蔓延?
人们就不知道细节了。
上世纪80、90年代,河南农村掀起 “快速致富,献血光荣”的风潮,许多村庄被卷入其中。在疫情最严重的上蔡县,人们将之称为“全民卖血运动”。
这里的“献血”“卖血”是一个概念,就是到血站出卖血浆。这与以往人们理解的“卖血”不同。以往卖血,是卖血人员到医院卖血, 直接用于医院病人临床输血。
实事上很久以来,底层社会长期存在着一批专业或半专业的卖血人群,中国的医疗体制中没有相应的供血机制,中国基层县乡医院没有血库,卖血的人就是医疗临床用血的“活的血库”。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农民就有人卖血,村民讲述当时情况:那时也有血头,叫血队长,医院有病人需要输血了,通知血队长找卖血的人,血队长知道有谁愿意卖血,就骑自行车来叫你。那时卖血的人少,也没有听说过传染艾滋病,有人卖了一辈子血,活到七八十岁。
1980年代后期,单采原料血浆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血液开始作为生物制品的原材料被收购,血液的市场需求急剧扩大。各地纷纷建血站专门采集原料血浆,一大批“献血员”队伍应运而生,河南农村一些贫困地区几乎所有青壮年被捲入其中。
为了有所区别,人们将到医院卖血,叫做卖全血,简称“全采”;到血站卖血叫做卖血浆,简称“单采”。
所谓“单采”,是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品生产厂家,生产制造生物制品,如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第八因子等等。因此,血站,准确称谓应当是“血浆站”或者“单采血浆站”。“单采血浆”有极其严格的操作技术要求,否则在回输血球的过程中,同一批卖血者中,只要有一个病毒携带者,就很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就是血站在“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的过程中,在卖血人员中传播开来,同时传播的还有疟疾、丙肝、梅毒淋病各种性病,等等多种疾病。
所以,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
而且当时许多献血员单采、全采都卖,所以,又出现大批“输血感染者”。疫区卫生防疫部门说:“北京上海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医源性根源都在河南。医生开一袋血浆提成5-10块,所以不管是否需要都动员病人输血,都是受利益驱动,结果输血又感染一批。”河南农民不是万不得已不舍得住院,妇女生孩子才会住院,当时许多住院产妇被动员输血,致使一大批产妇和孩子感染了艾滋病。
豫东南艾滋病高发区的卖血农民的确是穷,但是贫穷并不一定非要卖血,特别是卖血浆。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说:艾滋病都是单采才感染的,单采是政府开血站才开始的。要不是政府开血站,老百姓去哪卖血?不卖血咋会感染艾滋病?
艾滋病村的村民诸老二接受采访时非常强调这一点:“穷!成份贫农,一等一的贫农。分家时候就分了一袋子霉红薯片子。我不抱怨爹妈,穷!”“急啊!当个老百姓,计划生育罚着(越穷越生),给小孩子站房成媒(民风要聘礼要房才能结婚),老父亲有病,困难得很,见钱跟见命了一样。不然会死了活了去卖血么?”诸老二一家三代卖血。他13岁时父亲卖血,他本人18岁开始卖血,他的大儿子16岁,小儿子14岁开始卖血。全家有6个人感染了艾滋病:诸老二夫妇,两个儿子,两个儿媳。都是因为“单采血浆”。
同样感染了艾滋病的村民栗春营说:“我兄弟姊妹4个,染上艾滋病3个。当时我兄弟修车去了,不然也逃不掉。我们一家,我的父亲母亲,我和我老婆,俺姐俺姐夫,我妹妹妹夫还有一个外甥,都有艾滋病。受不下去,受不下去,有这个病痛苦得很!我父亲是吊死的!有一些时,我烧得受不了,买农药也想自杀。”
咋感染这么多人啊?
“家里穷,急,穷哩很!都说献血光荣,利国利民利己。就都去卖血。”
但是,即便是穷,也不一定必然要卖血。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诸老二后悔莫及、见了棺材才落泪,说:要不是卖血我身体好得很,也不怕掏力,拉架子车拉过3400斤,不是政府开血站,干啥不中,非去卖血?要说我卖血是因为穷,李宝安家可不穷,全村数他家过得好。有人找他借钱,宝安问一句借钱干啥?说做路费到开封去卖血,宝安说那我跟你一路去吧!就这!宝安就卖那一个血,感染了艾滋病,已经死罢好几年了。栗华中,小学毕业就出去打工,回来看村里人都卖血,几个年轻人打哄哄,玩哩一样,也卖了几个。除去挂号费、路费,一起吃吃喝喝花光了。“一吃一喝啥也不落,落了个艾滋病。”再说了,过去很早时候,村里就有人卖血,那时候都是全采,有人卖了一辈子血,活到七八十还好好哩,也没有听说过啥艾滋病。艾滋病都是单采才感染的,单采是政府开血站才开始的。
所以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说:都怨政府!要不是政府开血站,老百姓上哪去卖血?不卖血咋会得艾滋病?
村民们回忆说:那时候到处都是血站,开封就有5个血站。沈丘、项城、郸城、周口……都开血站!村里人就到处跑着卖血,不卖家少,都卖!县里小车下来宣传献血光荣,喇叭吆喝着:要致富,走献血路!自己县里有血站管献血,外县也有血站也管献血。“到最后,也不是不想买了,是找不到血站了。没有血站,上哪卖血?” 诸老二卖血一直卖到1998年,是全村卖血坚持到最后的一批人。2007年秋天,诸老二夫妇先后发病死亡。
河南农村艾滋病疫区,像诸老二、栗华中这样遭遇的农民很多。上蔡县疫情最严重的不是最闻名的文楼村而是后杨村,后杨村干部说:全村近4000人,1200多户,艾滋病死了300多人,普查时,还有感染者570多人,驻村工作队统计全村人口3210人,1800多人卖血,几乎家家都有人卖血(2006年)。沈丘县的银庄村,2600多人,600多户,1000多人卖血,也是几乎家家户户都卖血,有400多人感染艾滋病,至2011年12月31日,死亡245人。
驻马店是河南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全地区建了33个血站。再以后需要血浆量大了,乱收血浆,要求不严了,不合格也收。当地医院用血也从血站来的,临床输血用血,都没有检测手段。
人们说到当时的卖血乱相:办血站赚钱就跟拾钱一样,淨赚!那卖血的人群黑压压的,比唱大戏都热闹,血站的人忙得很,采血的人手上的茧子磨得跟铜钱一样厚。当时河南卖血,的确很乱。1995年政府砍血站之后,官办血站和一些私人血站转移地下继续非法采血。农民从响应号召卖血到偷着卖血,血站从化验检测到“胡采不验”,局面更加混乱,洗澡堂子、私家院落、猪圈里、庄稼地,哪里都是采血哩,老百姓有人是一手烧锅一手采血。确山县,一个拖拉机一早拉人去卖血,天灰濛濛看不见路,对面来一个车队,把一拖拉机的人都撞翻到河里,都没人伸头看看,17个人全淹死。人都麻木了。后来就发现有了艾滋病。有个老生产队长,为了给老婆治病,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芦岗乡一个大学生乡长,他家是南大吴上堂村的,才分去时当宣传秘书,2001年当上乡长。后来老是发烧,检查出来艾滋病,喝药自杀。南大吴高桥庄,20多岁的小姑娘上吊死了多少啊?社会就这,咋就卖血?!这种事太多了,说不完。感染艾滋病的太多啦。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王传宗,看见血站洗手池里溅得到处都是血,说简直就是屠宰场!吴仪来河南很生气,说血头血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卫生局高局长说杀谁呢?一方抢着献血换钱,一方还紧缺血源,两厢情愿。
一位基层卫生官员分析河南单采血浆传播艾滋病的背景和过程:传播艾滋病是因为办单采血浆站。这有一个国内外背景。艾滋病在非洲、欧洲、美国流行比较严重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国外就看好中国血液市场,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病。国际艾滋病流行惯例,都是由性传播。我国不同于外国西欧一些国家性开放。西欧保健品市场很大,利润很大,制造保健品原材料就是血液。那里的血液不敢用了,检测HIV成本太高。国外看好中国这个市场。另外国内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些相对比较落后地区解决温饱之后,当年拐回来发展经济。经过动员,讲解一些血的基本知识,卖血或者说献血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进行单采血浆工作,可以开展。所以当时国外都在中国建立生物制品所。国内一看单采血浆收益好,也盲目投资建厂,猛建!厂建起来就需要原料,就大量开发动员建立血站单采浆,卫生部出公文,要求一个县建一个血站。一开始这生意都好作,都建血站,也不需啥高新尖技术,抽了血以后搁离心机里一回就可以了,血浆提取出来,抽谁的血(红血球)回给谁,然后蛋白卖给厂家。但是底下建血站还是达不到规范要求。当时咱们国家市场经济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哪赚钱往哪挤,遗留问题不去想。1992年,基本各县都有血站。血站暴利。开始一天采一个血型,后来混着采,袋子装得太满,血溅出来交叉感染。后来私人血站更混乱,A型、B型乱套了。血站天天轰轰叫,俺单位(疾控中心,过去的防疫站)就办血站,当时单位的主要财源。河南的血走向全国6大生物制品所。买卖双方有利益驱动,一些生物制品所扩大,各个国家也投资,看好中国市场,大办血站采血,这就是单采浆献血这一块的历史。
就这样河南农民被动员起来走上献血的“光荣”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出卖自己的鲜血换取“资金”上交计划生育罚款,也盖房子娶妻生子,然后带着妻子孩子一起卖血;然后感染艾滋病被歧视鄙视;然后发病死亡,还被嗤之为愚昧无知,其实不是无知,是__。
可以说,河南农民因卖血引发的艾滋病灾难,是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完全没有竞争资本的农民以自己身体的血为资本捲入与市场的交换,所酿成的群体性的社会悲剧。
二 政府已经下令,但私下交易却难以禁止卫生部疾控司提供的报告显示,1995年,HIV的感染者人数由之前的几百例突增至1567例,其中有相当数量来自河南农村1995年以前的卖血人群。血液传播问题一下子突显出来。但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未知。尽管上个世纪80、90年代河南农民卖血已渐成风潮;至1990年代中期各种经血液传播的疾病已经暗流涌动;从1995年起,官方不断采取行动打击查封血站;至1999年我国“艾滋”上报数字连续第5年大幅增加,河南农村局部地区艾滋病疫情大规模爆发,青壮年占80%以上……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只是少数业内人士作为课题研究,外部社会毫不知情,甚至很重要的疫情报告在卫生防疫系统内部也不传达沟通。1990年代后期,河南农村一些地区的卖血农民已经开始发病死亡,但是也都处于蒙蔽状态,与相关信息完全隔膜,对正在来临的艾滋病灾难一片茫然。河南艾滋病疫情,很长时间处于社会资讯真空期。
诸老二和栗春营都反复跟我说着一句同样的话:“要是早知道卖血传染艾滋病,给多少钱也不卖血,要饭也不卖,打死也不卖啊!”后来我发现,这也是许多艾滋病村庄的人们反反复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是早知道……” 这样说时,他们都是满脸的懊悔与无奈。
一份河南CDC连续3年(1993-1995)对本省境内经省卫生厅验收合格的4县3市(包括濮阳县、兰考县、宝丰县、永城县、许昌市、洛阳市、开封市)七个单采血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的报告称:三年间共有588人份的血样呈HIV阳性。其中仅1993年就有542人份,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1993年全国的HIV阳性报告数274人。报告明确写道:“在献血浆人群中,不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还存在着严重的艾滋病的感染。
河南艾滋病疫情爆发导致中国艾滋病疫情形势风云突变。这七家经河南省卫生厅统一验收合格的血浆站已于1995年3月关闭。
这篇题为《河南省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检测结果分析》的专业医学检测报告,确凿无疑地证实了河南采供血传播艾滋病病毒至少在1993年已经开始,但是它的公开发表已经是在4年之后的1997年(苏惠存《疾病监测》1997年第12卷第7期)而且至今,河南当局卫生厅等相关部门,对此讳莫如深闭口不提。
而这项对“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监测”是对七家单采血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不是初检;且“七浆站”,多数并不在官方锁定的重灾区“豫东南6市13县”,更不属后来所规定的重点村“20乡38村”。这不能不使人担心河南艾滋病情势或许更为严峻。1992年10月,上海的生物制品厂家回馈河南省周口地区沈丘县血站数名献浆员的血浆 “HIV+”。
官方已经致力于整顿关闭血站,卫生厅下文勒令关闭,私人血站却开启
正是因为发现献血员中流行传播艾滋病,官方开始在部分地区整顿血站。最早从疫情最严重的驻马店地区开始。当地卫生官员说:1993年开始砍血站。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提出来,因为卖血的人都干不了活了,行署让血站停了。
河南省全面整顿血站,从1995年开始,媒体报导:“1995年3月,卫生部全国卫生厅局长紧急会议之后,河南省厅立即传达贯彻卫生部紧急会议精神,1995年3月31日发出明传电报,关闭全省所有单采浆站和血站的单采浆业务……。1995年5月4日,省政府在驻马店市召开7重点地市防控献血员HIV传播现场会,以政府名义下文在全省关闭单采浆站……”。
血站不让办了。“但是,1995年关血站,关不住!”当地卫生官员说。因为市场还需要血浆:一些生物制品厂才投资那么多建起来,还没有收回投资;一些原有生物制品所能扩大的也扩大了,还没见到收益。老百姓觉得把身体里的血抽出来洗干净再还给你,净化血液还挣钱……,卖血农民也觉得抽点血,又回(输)过来也没啥关係,还在卖血。私人血站地下兴盛起来!“到1995年国家砍血站,1995年下半年、1996年私人血站开始多了,感染人也更多了。”1996年3月14日河南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行动,大规模打击查封血站,卖血风潮大面上算是刹住了,有媒体称之为“3.14案件”。但是地下隐秘卖血一直延续到1998年。而此时,一些卖血农民已经开始发病死亡。
1998年,艾滋病村银庄已经不断有人发病死亡,村医以“疑似艾滋病”写报告给县乡防疫部门,县防保站来村里抽取血样检测,第一次9人中8人确证艾滋病。第二次13人,全部确证是艾滋病。这使乡防保站感到吃惊,他们说:照这种情况,全乡卖血人那么多,艾滋病得有多少哩?!
2001年县里向省里报告,全县卖血人员3—4万人,可以按20%感染率推算感染人数。省里没上报。当时县里负责卫生的主管副县长带着资料直接上了卫生部,卫生部大吃一惊。省卫生厅因此对县里很有意见。2001年卫生部来到县里,县里汇报“全民卖血运动”情况,陪同卫生部的省卫生厅副厅长不听汇报,嫌报告的数据太高,多次退回要求修改重报。那位主管副县长受到排斥,调任艾委会主任,有职无权。
直到2005年,艾滋病村的村医还是说:“1999年就确定是艾滋病了。……不过我也不能再给你说啥了,我是村医,领导知道了会批评,会说不想干回家!对记者采访要无可奉告,领导跟着时一点不敢说。”
“实实在在讲,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后果,否则谁也不会拿群众生命当儿戏,确确实实是认识不到。”在疫区,不止一个卫生官员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我相信这是实话。所有人都相信,没有人有意拿百姓性命当儿戏,都知道“人命关天”的分量。
虽然有少报现象,政府也已经引起了重视,但采血毕竟不是吸毒,甚至说面临中国许多城市的血荒,有很大需求。难道要每个村子的墙上刷上“献血容易得艾滋病”,或者警力像禁毒一样让每一个黑市交易都不发生。
三 追寻真相,但也要思考背后的东西“要是早知道卖血传染艾滋病,给多少钱也不卖血,要饭也不卖,打死也不卖啊!
如果卖血不会得病,农村人就应该用这种方式作为常态生活下去吗?
是不是所有人只要出身卑微,就有了错的不是我而是这个世界的理由。现在民智进步了,不像过去那些年,遇到事就都骂朝廷,丝毫不深刻思考。这事怪中央政府么,首先这届班子打掉了很多打老虎和苍蝇,如果了解细节肯定会认真合理的办理对待,希望愤青不要把绝妙的政令无法顺畅的传达到一个村而直接整体就开始喷中国,很多东西是历史的轨迹。这事全部让地方乡镇政府背锅?恐怕也不合适。一方水土一方人,有人然后有什么样的文化性格——村长、乡长,不能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么没良心的话来说,但是,非洲艾滋病情况更严重,给非洲一千万亿美金再配上一个华盛顿、林肯村长你觉得就都能解决了吗?
有些受害者拿到了补偿,变得好吃懒做,在村子里横行霸道,总是威胁用自己的血害别人,甚至成立艾滋讨债队从未失手过。或是借钱不还,或是霸占他人的妻子,要么就去别人家闹事儿。长此以往,竟过的“还算滋润”。我们在此谴责某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恶,但另一边,正在遭受恶行的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恶,甚至成为恶的一员。
艾滋讨债债队
一群艾滋病组成的催债队,已将业务发展到大江南北。记者找到了39岁的陈田红,很难想象,这个身高不到1.7米的干瘦男子,是百人催债队的领袖。他的队员,都是艾滋病人,并由他一手调教。大部分队员都是村民,90年代血浆生意兴起时,他们卖血养家而患上艾滋病,生活清苦,靠催债养家糊口。他还特别训练了一支几十人的娘子军,她们的年纪都是四五十岁左右,他叫她们“嫂子”。不论什么场合,“只要看见我的食指竖起来,这是一个暗号,她们就立马上去挠人”。
陈田红有一只专门接待客户的业务手机,铃声一响,他就知道生意上门。他几乎来者不拒,最火红时,一年能有上百个单子,他的标准是“不杀人放火、不触犯法律”。久经沙场后,陈田红已总结出完整一套“催债方法”。前几年,湖南一个大老板欠了巨额欠款,他带领十几个队员闯入老板办公室,亮出小红本,其威慑力,“比啥证都好使”,所有的人像避瘟疫一样缩到一边。
实际上,小红本是艾滋病医疗救治办公室发给患者的,相当于艾滋病人的“身份证明”。队员们往办公室里安静一坐,拉出“欠债还钱”的横幅,就如一个毒气场,所有人绕道而行。最开始,保安还会上来驱赶。队员们作势,卷卷袖子。保安就不敢再往前一步。“就算他们再忠心,也不会为了老板命都不要”,陈田红说,“这就是一场心理战,我们在这里一坐,所有人的心理压力一点点增加”。有些队员还会不定期“佯装”发病,在地上打滚干呕,口吐白沫,“周围的人吓得脸色惨白”。
他们几乎成了大老板的“贴身人”。老板上车,他们一前一后站在车头车尾,车纹丝难动;老板走路,他们就一左一右紧夹两侧,微笑有礼却打骂不走。大老板避瘟疫般逃到外地出差,几天后他下飞机回来,却看到陈田红已带了两个队员来“接机”了。陈田红迎上去,嬉皮笑脸说:“老板,我们来接您了,您辛苦了。”他很享受地看到,老板眼角耷拉、嘴角抽搐。
陈田红几乎断言,没有两天他们就可以收工了——这种表情他看过太多,这是思想高压已达到顶峰时的面部扭曲。果不其然,两天后,他们每个人拿着两三千的佣金,坐火车返乡。而像陈田红一样的催债队,在全国并不少见。本是弱势群体的他们,将自己活成了洪水猛兽,裹挟到催收江湖中——通常他们是最低端,却最危险的棋子,也是最后出招的“杀手锏”。
中国的农村变成什么样了?银行给他们低息贷款,这些农民花着明天的钱而没有丝毫规划,大手大脚,年底还不上钱就去贷款更多,贷款几次银行不给以后,就找自己的担保人要,几年下来,没人再借给他们钱,他们欠了几十万上百万,不是跑了就是上吊了。而那些本来用于耕种的钱根本用不到地方:土壤板结,粮食减产,投入产出根本不成比例。前期投入的,没有严格审批的贷款,最终只是成为滋生他们好吃懒做的土壤罢了。真实的情况永远比你看到的真实更魔幻,而这才是真正的底层残酷物语。